催眠術有著坎坷、漫長、帶有傳奇色彩的歷史。從迷信到科學,從表演到實用。催眠術可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年,麥斯麥(Mesmer)被認為是催眠術的開山鼻祖,他認為在天體、地球和身體三者之間存在一種可以感受到的力量,它似乎是一種流體,可以在任何物體之間傳遞磁力,磁力產生的效應能被人體的神經系統直接感受到,因此可以治療神經系統的疾病,但Mesmer的催眠術帶有神秘的巫術色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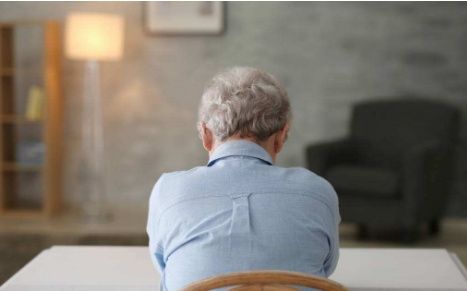
布雷德(James Braid)被認為是現代催眠術之父,他通過提出催眠的物質基礎而結束了催眠術神秘化的巫術時代。他認為,催眠是一種特殊的類睡眠狀態,是視神經疲勞所引起的睡眠,流傳較廣的催眠球便因此發明。他同時將催眠研究的焦點從外在力量轉移到內在效應上,認為催眠的核心力量是暗示。
Jean - Martin Charcot 創建了以精神病理學為基礎的“巴黎學派”,將歇斯底里障礙和催眠的癥狀聯系在一起,得到醫學界的認可。 Pierre Janet(1901, 1907,1925)受巴黎學派的影響,發展出最初的解離概念( dissociation )。在解離狀態下,頭腦中的某些部分與其他有所區分,并且與意識和自動控制分離。與“巴黎學派”持續論戰的“南錫學派”以心理學為基礎,認為催眠產生于心理的運作,并強調“暗示”的力量。 兩個學派持續爭論,也為催眠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聲音,但兩者都對認知加工過程標準化認可。
Clark Hull(1933)認為,盡管存在所謂催眠解離的可能性,但并不存在兩種刺激內在加工過程功能上的獨立。 他通過實驗方法來解釋催眠,發現高暗示性可以最好的解釋催眠。
Ernest R. Hilgard 及團隊研制了“斯坦福催眠感受性量表”( SHSS),認為存在一定百分比的人對催眠存在由遺傳確定的易感性,而且這種潛能會保持相對穩定。他的學生 Milton H. Erickson 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催眠治療大師之一,他的催眠理論堅持一個信念:在人類的潛意識里蘊藏著巨大的潛能。他建議采用自然主義的催眠方法,提倡從關系中對現象進行觀察。他的催眠技術能靈活利用來訪者本身的阻抗、困境,以及通過幽默、重構、驚訝、隱喻等多種手法來達到治療目的。
20世紀50年代晚期,以Wolpe(1958)為代表的行為主義治療師開始將催眠整合到系統脫敏等治療方法中,行為主義治療師去除催眠誘導部分而直接應用放松技術。正念療法的興起不經意間帶動了催眠的復興,使用催眠與正念治療抑郁癥的Yapko(2011)指出,催眠的根本目的是創造一個情境,在這個情境中來訪者得以探索、吸收新的意識水平,并具有轉變個人經驗的可能性,對暗示或信息進行無評判但卻有方向性的接收。
Emest Rossi 是 Erickson 的伙伴,他提出了以催眠治療為手段來促進心- 腦治愈的整合方法,對神經催眠實踐做出了獨特的貢獻。通過整合腦環路的自然機制,Rossi發展出一套使用催眠促進心-腦-身自然康復的創造過程。Rossi 第一次在催眠領域提出身體、心理與環境間的關系,同時也與當代具身認知的鏡像神經元理念不謀而合,這為催眠未來的發展提出無限可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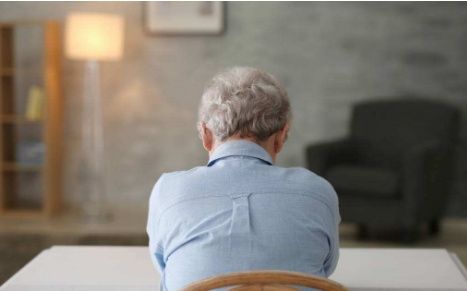
 成都心理咨詢網站
成都心理咨詢網站